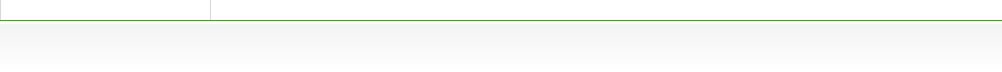埃皮达鲁斯剧场是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古希腊剧场之一,中央的圆形演出台直径20米,加上看台的面积近14平方千米,至多可容纳14000名观众,这相当于十多个400米跑道标准中学操场的体量之和。演出人员分为两类:演员和歌队。饰演个体角色的演员通常不超过3人,歌队就要庞大得多了,少则12人,多则50人。从现代观众的体验来看,古希腊戏剧类似于体育场中举办的明星演唱会。
歌队在希腊语里读作chorus,现在经常翻译成“合唱队”。不过,从功能的角度来看,歌队与我们熟悉的合唱队大相径庭,而类似于旁白、捧哏或伴舞。比如在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中,歌队扮演波斯都城的长老。他们一开场便极尽铺排之能事,渲染远征希腊的波斯大军之雄壮:“亚细亚的全军出征去了……当中有麦加巴忒斯和阿塔拍斯几员大将,他们本是国王,却来向波斯大帝称臣。他们统率着车骑与弓手向前猛进,他们的志气很坚强,在战场上真是威风凛凛!”接着,他们又扮演起了“捧哏”的角色,为波斯太后阿托莎解说不祥的梦,一步步引出演员的情绪和故事的主题。歌队贯穿全剧,跟随着整部剧的情节不断推进,时而提供必要的背景信息,时而推动情节发展。此外,歌队还要排练整齐协调的动作和表情,表达出恰当的情绪。
但即便是这样来描绘,也只是得其形而失其神,主要在于两点。第一,歌队成员代入角色极深,就不要说现代影视作品里的旁白或画外音了,即便是老戏骨也未必比得上。正如尼采在中所说,“希腊歌队必须把舞台形象当作真人。扮海神女儿的歌队就要真的相信自己亲眼看见普罗米修斯,并且认为自己就是剧中的真神。”当然,这未必意味着现代演员的技艺不如古人。毕竟,早期的歌队都是由普通公民组成的。这里的关键在于,当代影视媒介的内核是讲故事,观众和演员自始至终都清楚地知道:故事只是故事。因此,有时演员太过入戏时还会被批评做作。古希腊戏剧的要旨则在于情绪,大多取材于神话故事的悲剧尤甚。观众来到剧场之前往往就知道情节梗概了:普罗米修斯会被钉在高加索山上,美狄亚会亲手掐死自己的孩子,违令为兄长收尸的安提戈涅会被处死。观众追求的是一种融合了沉浸感与距离感的体验。悲剧会有意识的使用超越日常用语的“诗性语言”,从而唤起一个让观众超越自身的世界。与此同时,歌队成员的核心也不是“推动情节”,而是亲身经历一连串跌宕的情绪起伏。用德国古典学者维尔纳·耶格尔(WernerJaeger)的话说,“剧中的一切都被带入了一个崇高形象和虔诚敬畏的世界。”
由此便引出了古希腊悲剧的第二个特征:它是一种公共活动,或者说“仪式”,而不是娱乐消费品。职业化歌队是在公元前4世纪出现的,当时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早已作古。在此之前,戏剧在古希腊都是一种全民性的活动。公民经过漫长而艰苦的集体排练,在舞台上,在全体同胞面前短暂地营造出崇高的幻境,将上万人笼罩在一种迷乱与庄严并行不悖的气氛下。难怪耶格尔会说,“悲剧曾在城邦鼎盛时对其加以神化,在其崛起时提供了内在的支持和力量。……在同时代人的感受中,悲剧的本质和影响从未仅仅被理解成美学的。对他们而言,悲剧如同国王,要对整个城邦的精神负责。”当然,当时的希腊戏剧中心雅典已经在迈向民主时代,希波战争更为雅典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耀。城邦的法律不再由国王或僭主颁布,他们也无法再主宰公民的心灵。正是在这道洪流中,戏剧崛起为城邦的盛事与公民的学校,把握和塑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
文化的教育功能并不是古希腊——具体来说,是公元前5世纪至4世纪中叶的古典时代——所独有的。比方说,子夏在《毛诗序》中就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在这里,教化以人际关系为对象,宗旨是营造和维护和谐的社会氛围。这种教化施加影响的手段则有两种,共情与示范。一方面是激发天然的情绪,从而形成情感的共同体,另一方面是描绘人们应当遵循的规范。直到今天,我们谈到“教化”或者“熏陶”,主要也是着眼于此。这种思路通常要预设一套公序良俗,文化是达到这种理想社会秩序的手段。在古希腊文明中,《荷马史诗》所在的古风时代基本就是这种状况。
但是,到了以戏剧、民主、哲学为核心成就,以索福克勒斯、伯里克利、苏格拉底为代表人物的古典时代,一种新的“教化”演化形成。而这正是耶格尔在《教化:古希腊的成人之道》中所要探讨的全新概念。在他看来,教化(Bildung)是“通过创造具有内在完善性和特质的理想典型来塑造人。”这就是说,那一代人在追求人应有的样子。在这个过程中,探索与教育不仅仅同步发生,更可以说是一体两面。
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悲剧中的“理想人物”并不是简单的榜样模范,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应当模仿的对象。就拿“盗火者”普罗米修斯来说吧。在比埃斯库罗斯早200多年的赫西俄德笔下,普罗米修斯是一个在神力面前败下阵来的秩序破坏者。虽然他善良且足智多谋,但“欺骗宙斯和蒙混他的心志是不可能的”。而在近代以来的演绎则完全颠倒过来,普罗米修斯是理想主义的启蒙者乃至革命家,宙斯则是施行策的专横暴君。
相比之下,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或许可以放在两者之间。在赫西俄德那里,普罗米修斯有点像斗法失败的闻太师,又有些像屡教不改的调皮孩子。宙斯的力量体现在一次次单独的较量中。而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宙斯从未登场,但他的“严密法度”却弥漫在每一行诗句中。在诗人眼中,神代表的正义秩序与盗火行为的开创意义并行不悖,统一在普罗米修斯的无限痛苦中,构成了全剧的情绪力量源泉。
同时,这也是古希腊悲剧教化人心的一种方式。在剧中,歌队是普罗米修斯岳父——河神俄刻阿诺斯的十二个女儿,来到被绑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身旁,试图看望和慰藉他。在整部剧中,她们一直在恐惧与同情之间拉扯,并在这种难熬的摩擦中产生了痛苦的清醒认识。比如,在听完普罗米修斯哀叹自己教会了人类一切技艺,自己却拗不过命运后,歌队唱道,“普罗米修斯,我看见你这可怕的命运,懂得了法则。我现在听见的是不同的声调啊,和那次我给你贺喜,绕着浴室和新床所唱的调子多么不同啊!那时节你带着聘礼求婚,把我的姐妹赫西俄涅接去作同衾的妻子。”而在全剧的末尾,歌队尽管受到神的警告,却依然心甘情愿地陪着普罗米修斯堕入地狱,“普罗米修斯在雷电中消失,歌队也跟着不见了。”在一次次紧张的冲撞后,情绪终于升华为至高的智慧。
今人阅读剧本时,凭借共情与想象力能够依稀体会到这出剧在希腊剧场中带来的震撼。但相比于长期排练后终于登台的歌队成员,这种体验基本只能停留在软弱的理性层面,而达不到真正的动人心弦。即使有一群专业演员,在类似的场地中重演《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恐怕也是无益的。古希腊悲剧打动观众的关键在于,演员、歌队和观众共同进入了一个超越凡俗的领域。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意境类似于迪士尼乐园致力于营造的“魔幻时刻”,但那里的“魔幻”显然过于阳光和扁平了,充其量与人脑愉快中枢在同一个层面。
鲁迅有一句名言,“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这句话放到古希腊喜剧中同样颇为恰切。不同于自始至终追求崇高与超越的悲剧,喜剧是一种贴近现实的艺术。它的起源可能是歌队对观众的嘲讽,就像今天的脱口秀演员会不时跟观众开玩笑一样。不过,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那么古希腊喜剧,尤其是号称“古希腊戏剧之父”的阿里斯托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毕竟,优伶劝谏是一个普遍存在于古今中外社会中的现象:《史记》中有《滑稽列传》,美剧《冰与火之歌》中的弄臣月童也敢在宴会上嘲弄在场的达官贵人,甚至连总主教都不放过。
古希腊喜剧的成就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随着雅典民主制的兴起,社会言论环境日益宽松,本性上倾向于讽刺一切的喜剧开始走上公共领域,扮演起了新的角色。用耶格尔的话说,“带来自由的民主出于内在的必要性而为精神自由设立了边界……作为这种城邦的本质,设立边界的工作并非由当局,而是由舆论战来完成。喜剧在雅典承担着监察之职。”
监察的另一面就是教育。没有人愿意听脱离现实的死板说教,即便是巍峨超凡的埃斯库罗斯悲剧,它也必须调动强烈的崇高与庄严感。假如普罗米修斯只是一味地宣扬,“我们要打破可恶的旧制度,创造人类的光明未来,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到来!”那么,就算是在僭主统治下的雅典,人们也不会产生任何共情。在这一方面,紧跟现实的喜剧有天然优势,在有力的作者笔下能够成为批判的武器。
有趣的是,教育问题本身也是古希腊喜剧的一个热门题材,比如阿里斯托芬的《云》。剧中有两位人物,分别叫“正理”和“歪理”。正理代表的是几百年前《荷马史诗》年代的教育观,强调坚忍不拔、尊师重道、尤其是不要用诡辩歪曲先人的智慧。歪理则代表着新兴的智者学派,从古代神话和现实政治中旁征博引,向年轻人宣扬节制意味着放弃愉悦,放下包袱反而能够带来大的利益。乍看上去,阿里斯托芬似乎颇有怀古之思,但讽刺的是,他在剧中熟练运用了他所批判的种种“诡辩”手法,这一点清楚地表明了他是自己所处的时代的产物。正如耶格尔所说,“阿里斯托芬不是教条式的强硬反动者。不过,被时代的猛烈风暴裹挟前行和目睹宝贵旧文化的消失(同样宝贵的新文化尚未确立)引发的情感在那个过渡时期强烈爆发了,让关注这一切的精神充满了畏惧。”
这里所说的“旧文化的消失”,指的或许并不是人们不再信奉《荷马史诗》里的英雄。他生活在一个战争与政变频仍的年代,雅典失去了希腊盟主的地位,悲剧剧场日渐荒芜,喜剧则在那段日子里成为了城邦精神的镜子与寄托。阿里斯托芬在晚年作品《蛙》中借冥王之口说:“祝你一路平安,埃斯库罗斯,前去用有益的建议拯救城邦,并教育愚人,因为他们数量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