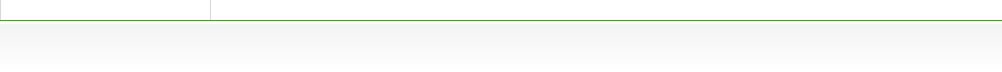【按语】 在西方哲学史上,“理论哲学”历来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享有“第一哲学”的美誉。诚然,一如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所说,毕达哥拉斯是“第一个”讲“道德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西方哲学家,但由于他最终将“道德”和“实践哲学”“还原”或“归结”为“数”,从而最后还是将他的“道德哲学”或“实践哲学”奠放在“理论哲学”的基础之上了。亚里士多德虽然以“真假”和“善恶”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划界”,但他最后还是从“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角度出发,将研究“最初本原和原因的思辨科学”或“理论科学”称作“最高科学”或“在诸科学中占最主导地位的科学”。莱布尼茨“实践哲学”的根本使命即在于以“实践哲学重于和高于理论哲学”的哲学公式向西方哲学的传统模式发起挑战,以期构建一种新的以实践哲学为主旨和圭臬的哲学。本《实践哲学文集》收入了莱布尼茨有关论文和短信25篇,为段德智教授主编的10卷本《莱布尼茨文集》第8卷。其要点如下:(1)莱布尼茨提出并论证了“实践哲学”高于并重于“理论哲学”的观点,从而颠覆了理论哲学历来享有至高无上地位的西方哲学传统;(2)莱布尼茨的实践哲学始终贯穿着两项最基本的原则,这就是“理性原则”和“自由原则”;(3)莱布尼茨不仅将“自由”规定为他的实践哲学的中心范畴,而且还对他的“自由”概念的“三重根”,即“理性”、“自发性”和“偶然性”,做过相当深入和系统的阐述;(4)“自然法”乃莱布尼茨实践哲学的“第一原则”;他强调自然法的基本源泉在于“具有理性本性的永恒法”;(5)莱布尼茨的实践哲学大体包含四个板块,这就是“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他这个法学博士是西方法学史上提出“法哲学”(Rechtsphilosophie)概念的第一人)和“宗教哲学”;其中,有关其“宗教哲学”的论述将放入莱布尼茨的《宗教哲学与自然神学文集》一卷(即《莱布尼茨文集》第9卷)。所有这些,不仅可以视为本文集的“要点”,也可以视为“编译者前言”的要点。
如所周知,莱布尼茨在西方哲学史上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黑格尔在谈到莱布尼茨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时,曾经非常中肯地指出:“笛卡尔和斯宾诺莎提出了思维和存在,洛克提出了经验,提出了形而上学的观念,并且论述了对立本身。莱布尼茨的单子,是集这类世界观之大成。”[1]现代西方大哲罗素,不仅将莱布尼茨视为西方哲学史上的“伟大人物”,而且还特别强调了莱布尼茨哲学的现代意义,指出:“他的伟大现在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明显。”[2]罗素对莱布尼茨在符号逻辑或数理逻辑的开创之功尤为钦佩。他在《西方哲学史》中写道:“按数学家和无穷小算法的发明者来讲,他卓越非凡,这且不谈;他又是数理逻辑的一个先驱,在谁也没认识到数理逻辑的重要性的时候,他看到了它的重要。”[3]作为现代数理逻辑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罗素心悦诚服地宣称:“莱布尼茨坚信逻辑不仅在它本门范围内重要,当作形而上学的基础也是重要的。他对数理逻辑有研究,研究成绩他当初假使发表了,会重要之至;那么,他就会成为数理逻辑的始祖,而这门科学也就比实际上提早一个半世纪问世。”[4]
但人们对莱布尼茨哲学的赞颂似乎只限于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和数理逻辑思想等方面,只限于他的理论哲学。尽管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莱布尼茨不仅在理论哲学有极高的造诣,而且在实践哲学领域也同样有极高的造诣。但长期以来,许多莱布尼茨研究者尽管对他的理论哲学赞誉有加,但一论及莱布尼茨的实践哲学便马上翻脸,不是无视它的存在,就是竭力贬低。
在无视乃至贬低莱布尼茨实践哲学的学术价值或学术地位方面,罗素无疑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例证。我们知道,在其漫长的哲学生涯中,罗素先后获得了多重身份,他最初是一位“新黑格尔主义者”,之后成了“逻辑原子主义者”,最后成了“中立一元论者”。但有一个身份是他一辈子都承认并且享有的,这就是“莱布尼茨哲学专家”。在其于1945年出版的《西方哲学史》的“美国版序言”里,罗素堂而皇之地宣布:“对研究我的庞大题材中的任何一部分的专家们,我还该说几句辩解的话。关于任何一个哲学家,我的知识显然不可能和一个研究范围不太广泛的人所能知道的相比。我毫不怀疑,很多人对于我所述及的任何一个哲学家,——除了莱布尼茨之外——都比我知道得多。”[5]作为一位莱布尼茨专家,罗素在他的许多著作(如《我的哲学的发展》《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西方哲学史》《罗素自传》等)里,屡屡论及莱布尼茨,但《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无疑是他全面系统批评性阐释莱布尼茨哲学的唯一一部哲学专著。然而,正是在这样一部全面系统阐释莱布尼茨哲学思想的学术专著中,我们一目了然地看到了莱布尼茨对莱布尼茨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明显不过的畸重畸轻。我们知道,罗素的这部专著除“序”和“附录”外,共含16章。其中前15章讲的全是莱布尼茨的理论哲学(包含莱布尼茨的逻辑学、形而上学、物质哲学、认识论和“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等),仅在最后一章才论及莱布尼茨实践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莱布尼茨的伦理学”。就章节论,这部专著阐释莱布尼茨实践哲学内容的章节与其阐释莱布尼茨理论哲学内容的章节之比为1:15。依据乔治•艾伦与昂温股份有限公司(George Allen & Unwind Ltd)1958年出版的版本,正文16章计202页,其中阐释莱布尼茨理论哲学的15章有190页,占比超94%,而阐释莱布尼茨实践哲学的第16章则只有12个页面,占比不足6%。即使将正文中的第15章,即“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一章计入“实践哲学”,情况也不会发生很大的改变。照此,阐释莱布尼茨理论哲学的14章有171页,占比超84%,而阐释莱布尼茨哲学的第15-16两章也只有31个页面,占比也依然不足16%。我们从后文中马上就可以看出,罗素对莱布尼茨实践哲学的这样一种轻率处理,不仅有违莱布尼茨的哲学初衷,而且也相当主观随意地一笔勾销了莱布尼茨在政治哲学、法哲学和宗教哲学等实践哲学领域所做的种种努力和重大成就。
不仅如此,罗素对莱布尼茨实践哲学的“无视乃至贬低”还典型地体现在他对莱布尼茨实践哲学的理由不甚充分的“批评”上。例如,罗素批评莱布尼茨对伦理学“不经心”(indifference)[6]便很难服众。因为人们很难想象:倘若一个人对“伦理学”“不经心”,他何以可能郑重其事地宣称“美德乃依据智慧行动的习惯”,“智慧”作为“一门关于幸福的科学”是“首席科学”,“爱人就是在他人的完满性中找到快乐”,“幸福是一种持久的快乐状态”。[7]再如,罗素在“莱布尼茨的伦理学”这一章里声称:“虽然我只想大略地论述一下这个题目,但还是要给它适当的篇幅,使之与这一问题在莱布尼茨沉思中所占的位置成比例。”[8]但从实际情况看,罗素的这样一个说法多少有言过其实之嫌。因为虽然莱布尼茨在本著中表明,他在写这本书时,着重参考了“格本”(格尔哈特于1875—1890年编辑出版的《莱布尼茨哲学著作集》)、“邓本”(邓肯于1890年编辑出版的《莱布尼茨哲学著作集》)、“拉塔本”(拉塔于1898年编辑出版的《莱布尼茨:单子论及其他哲学著作集》)和“新论”(兰利于1896年翻译出版的《人类理智新论》)等,但他在写作《批评性解释》时显然并未将莱布尼茨的有关主要哲学主张都囊括进去。例如,莱布尼茨在《人类理智新论》第1卷第2章中所强调的“道德比算术更重要”,[9]对于我们深刻理解莱布尼茨的“道德哲学”乃至他的实践哲学思想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却由于其不合罗素的哲学口味而置之不理。再如,莱布尼茨在《新论》第4卷第21章所使用的“实践哲学或道德”(la Philosophie practique ou la Morale)的措辞,对于我们深刻理解莱布尼茨的“伦理学”思想无疑大有益处,却也同样由于其不合罗素的口味而被弃之不顾。罗素抱怨莱布尼茨的伦理学“平庸”,[10]其实他本人极力将莱布尼茨伦理学平面化的种种做法或许正是招致其“平庸”和肤浅的根本造因。
在《批评性解释》的最后一章里,罗素还为莱布尼茨罗列了一个“迁就基督宗教道德家”、“凡涉及教会的地方,就以一个辩护无知和蒙昧主义斗士的面孔出现”的罪名。[11]在阅读莱布尼茨的论著中,我感觉莱布尼茨在处理信仰和理性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与洛克同样主张“信仰超乎理性但不能反乎理性”,在同情自然神论方面,他似乎比洛克还要激进一些。[12]罗素把莱布尼茨说成是“辩护无知和蒙昧主义斗士”,显然有违事实,言之过重了。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罗素在写作《批评性解释》时,并未认真读过莱布尼茨的《神正论》。因为莱布尼茨在其中反复强调的是“信仰与理性的一致”而非“理性与信仰的一致”,是信仰尽管可以超乎理性,但绝对无权反乎理性,从而一笔勾销了信仰对于理性的任何意义上的“否决权”,捍卫了理性或理性法庭的尊严。莱布尼茨断然宣布:“无论是罗马天主教神学家,还是新教神学家,当他们深入探究这一问题时,便都承认我在前面刚刚阐述的那些原理。所有被说成反乎理性的东西都是没有任何力量的,除非其反对的是一种所谓的理性,受到了虚假现象的玷污和欺骗。”[13]既然如此,倘若将这样一位思想家和哲学家说成是一个蒙昧主义的辩护士,未免失之牵强。
平心而论,《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作为一部“哲学”著作,它对其主要论题即“莱布尼茨哲学差不多源于他的逻辑学”的论证和“批评性解释”是相当成功的。但该著作为一部“哲学史”著作,特别是该著对“莱布尼茨的伦理学”的批评性解释,显然失之偏颇和武断。[14]如前所述,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曾经把莱布尼茨说成是哲学史上的一位“伟大人物”,但在《批评性解释》里,在谈到莱布尼茨的“伦理学”时,他竟然用“一团矛盾”(a mass of inconsistencies)予以概括,[15]人们很难从罗素对其“伦理学”的“批评性解释”中看到“伟大哲学家”的一点点踪影。
问题在于:罗素并非一个普通哲学家,而是一位现代西方哲学大家,他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后世研究,特别是他对莱布尼茨道德哲学乃至莱布尼茨整个实践哲学的后世研究无疑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消极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莱布尼茨实践哲学领域至今还笼罩在罗素的阴影之下。例如,《批评性解释》出版70多年后,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和法哲学家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就在一篇题为“莱布尼茨对法律、政治和国家的哲学反思”的论文中宣布“在法学和政治学领域”,莱布尼茨并不是“一个一流思想家”。[16]这就意味着:莱布尼茨不仅如罗素所说,在“伦理学”领域毫无建树,而且在“法哲学”和“政治学”领域也没有取得任何值得关注的成就。
然而,贬低和抹黑莱布尼茨实践哲学(包括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这样一类做法也遭到了一些莱布尼茨专家的谴责。例如,莱布尼茨专家、英国开放大学教授斯图尔特•布朗(Stuart Brown)便不屑于这样一种做派,斥之为“让人非常泄气的评估”(this rather deflationary assessment)。布朗驳斥说,尽管莱布尼茨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我们必须说”:他为传统的法学智慧和政治学智慧“提供和展现了一种深刻的创造性的哲学根基”(he developed a profound and inventive philosophical underpinning)。[17]其实,在一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布朗对弗里德里希的这样一个批评移用到罗素对“莱布尼茨伦理学”的批评上。因为我们同样有理由说:罗素把莱布尼茨的“伦理学”概括为“一团矛盾”的说法是一个“让人非常泄气的评估”,尽管莱布尼茨的伦理学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他毕竟为传统的伦理智慧“提供和展现了一种深刻的创造性的哲学根基”,将其提升到了“道德哲学”的层面和高度。
其实,尽管弗里德里希并未深刻理解莱布尼茨对法律、政治和国家问题的“哲学反思”,我们也不妨将其使用的“哲学反思”这个短语视为他那篇论文的一个亮点。因为莱布尼茨之所以能够成为如罗素所说的“伟大人物”,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他那个时代的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而且还因为他对其所掌握的百科全书式的科学知识(包括种种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都进行了切实的“哲学反思”,为它们“提供和展现了一种深刻的创造性的哲学根基”,从而对其有一种高屋建瓴的理解和把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总体上看,无论就知识的博大,还是就知识的精深,他都是他那个时代无人企及的大家。也正是凭借这样一种“哲学反思”,凭借着他的过人的学养、气质和功夫,莱布尼茨才得以将普通人文学科意义上的伦理学、政治学和法学提升到了“哲学”层面和高度,将其提练成作为“实践哲学”分支学科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尽管就伦理学、政治学和法学的单个领域看,无论是从莱布尼茨所在的时代看还是从历史上看,都有许许多多的学者的成就高于莱布尼茨,但若就将所有这些学科提升到“哲学”层面,将其锻造成“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并进而将其统摄到“实践哲学”之名下,至少直至莱布尼茨时代尚没有一个学者取得无如此辉煌的成就。无论如何,罗素对此是缺乏认识的。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一条重要结论,这就是:为要对莱布尼茨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思想有一种切实的理解和把握,我们首先就必须跳出传统伦理学、政治学和法学的狭隘论域,逐步上升到莱布尼茨实践哲学的“绝顶”。否则,单单就事论事,就事论理,就会像印度“瞎子摸象”的寓言所昭示的那样,非但不能对整个大象有一种总体的了解,而且即使对大象的耳朵、腿和鼻子等各个部分也不可能有真实的认识。我国古代哲理诗人苏轼曾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即是谓此。既然如此,我们在对莱布尼茨的作为其实践哲学分支学科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做出扼要的解说之前对莱布尼茨实践哲学的宏观构想先行地做出一个扼要的说明就很有必要了。
在莱布尼茨实践哲学的宏观构想中,最富有创意的当属他对实践哲学的学科定位:首次突破了传统哲学的成规,提出了实践哲学重于和高于理论科学的理念。
我们知道,直至莱布尼茨时代,在西方哲学史上,理论哲学一直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诚然,西方哲学史上的实践哲学可以一直上溯到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因为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不仅像米利都学派那样“掌握了意识的实践本质”,而且还致力于“道德神圣化”,将数学和米利都学派推崇的“自然哲学”知识作为其“道德神圣化”的手段,从而使道德实践直接获得了“哲学”的意蕴,被提升到了本体论的层面。《希腊思想》的作者罗斑在谈到毕达哥拉斯的这样一种努力时写道:“毕达哥拉斯被认为是‘哲学’一词的发明者,‘哲学’亦即‘趋向智慧的努力’,这恰是道德神圣化的一个因素。那些已得门径的人之致力于数学、天文学、音乐、医学、体育及荷马、赫西俄德的评注阅读,正是因为他们把这些研究看成是不同程度上的纯化灵魂,并相对地纯化身体的手段。”[18]也许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称赞毕达哥拉斯是“第一个”试图从哲学的高度“讲道德”的人,而黑格尔则称赞他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讲“实践哲学”的人。[19] 但是,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大伦理学》第1卷里所批评的那样,毕达哥拉斯虽然“第一个”试图从哲学的高度“讲道德”,“但是并不是以正确的方式讲;因为他由于把道德还原为数,所以不能建立线]这就是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毕达哥拉斯归根到底还是把他的“道德哲学”或“实践哲学”“还原”成他的主张“数乃万物始基”的理论哲学了。
应当说,在这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认真汲取了毕达哥拉斯的教训。为了避免落入毕达哥拉斯的“还原论”,亚里士多德着重从思维功能、存在者中的对象域和学科旨趣三个方面入手对理论哲学(理论科学或理论知识)和实践哲学(实践科学或实践知识)做出了明确的区分。首先,从思维功能看,理论哲学是一种纯粹“认识的思维”和“静观的思维”或“思辨思维”,而实践哲学则是一种“计算性思维”和“实践思维”或“筹划思维”。[21]其次,从存在者中的对象域看,理论哲学既然是一种“认识的思维”和“静观的思维”,其对象也就无关乎人的行动,就是自然事物中永恒不变的东西,而自然事物运动和静止的本原也就存在于这些自然事物的自身之中,而不存在于实践者之中,我们因此也就不可能对它们进行任何实践改造活动,我们即使将一块石头抛上天空一千次,我们也不可能使之习惯于上升而不至于下落。相反,实践哲学的存在者中的对象则不是普遍的和永恒不变的东西,而总是具体可变的东西,其运动变化的本原则不存在于对象自身之中,而是存在于实践者之中。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强调说:在理论哲学中,我们思考的是“存在者中那些其本原不可以是别样的东西”,但在实践哲学中,我们思考的却是存在者中那些“可以是别样的东西”,因为“没有人筹划那些不可以是别样的东西”。[22]最后,从学科旨趣看,纯粹理论哲学的旨趣仅在于分辨真假,而实践哲学的旨趣则重在褒贬善恶。诚然,无论是理论哲学还是实践哲学都有一个思考问题,但其思考的内容和目标却显然有别:理论哲学的思考“只有真假而不造成善恶”,而实践哲学思考的线]鉴此,我们不妨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哲学说成是讲“真”的哲学,而把他的实践哲学即伦理学和政治学说成是讲“善”的哲学,只不过他在他的伦理学里讲的是一种“个人善”,在他的政治学里讲的则是一种“公共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尽管藉思维功能、存在者中的对象域和学科旨趣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之区分,规避了毕达哥拉斯的“还原论”错误,他却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这两门哲学进行价值判断的权利,依然像毕达哥拉斯那样,固守理论哲学优先的立场。例如,在《形而上学》里,亚里士多德把“形而上学”即作为研究“最初本原和原因的思辨科学”,称作“最高科学”、“自由科学”和“在诸科学中占最主导地位的科学”,亦即“第一哲学”。[24]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亚里士多德从人是理性动物的高度进而明确地提出了“知德”高于“行德”的观点,断言:“思辨是最高贵的活动。因为灵智在我们灵魂内部是最高贵的,而灵智的对象在整个认识领域内又是最高贵的东西。”[25]亚里士多德这种理论哲学高于实践哲学的观点对后世哲学产生了极其深广的影响。
至近代伊始,人们非但没有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向前推进一步,反而在一个意义上出现了毕达哥拉斯实践哲学借尸还魂的场面。享有“近代哲学之父”盛誉的笛卡尔提出了一种“进一步退两步”的哲学观。如前所述,依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实践哲学虽然与理论哲学也有某种关联,但由于其在思维功能、存在者中的对象域和学科旨趣三个方面明显地区别于理论科学,故而无论如何我们也不可能将其由理论哲学直接推演出来。但在笛卡尔这里,事情却出现了根本性的扭转,实践科学(实践哲学)像是由理论科学(“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直接产生出来的一样。我们知道,笛卡尔对哲学有一个著名的“树喻”。按照他的说法,“整个哲学就像一棵树似的,其中形而上学是树根,物理学是树干,由这个树干生长出来的各个树枝就是所有别的知识分支。这些分支可以归纳成三门主要的科学,这就是医学、机械学和伦理学”。[26]在这段话里,笛卡尔所说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显然属于“理论科学”或“理论哲学”的范畴,而他所说的“医学、机械学和伦理学”则明显属于“实践科学”或“实践哲学”的范畴。[27]既然如此,则当笛卡尔宣布说:“医学、机械学和伦理学”这些“树枝”都是由“物理学”这个“树干”“生长出来”的“知识分支”的时候,他也就是在宣布:“医学、机械学和伦理学”这些“实践知识”或“实践科学”统统都只不过是由“理论科学”或“理论哲学”直接“生长出来”或派生出来的。而这也就进一步意味着,在笛卡尔这里,实践科学或实践哲学业已丧失了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享有的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最终还是像毕达哥拉斯“把道德还原为数”那样而被笛卡尔“还原”成了“理论科学”(首先被还原成了“物理学”,进而又被还原成了“形而上学”)。毋庸讳言,笛卡尔在《哲学原理》中确曾使用过“伦理学”乃“心志最高尚也最完满的道德学说”(altiffimam autem ces & perfectiffimam morum intelligo)这样的短语,[28]但当笛卡尔这样说时,他针对的是作为哲学大树“果实”部分的“三门主要的科学”即“医学、机械学和伦理学”说的,而不是针对派生这些分支科学的作为“树干”的“物理学”说的,更不是针对派生作为“树干”的“物理学”和作为“果实”的“医学、机械学和伦理学”的作为“树根”的“形而上学”说的,从而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的学科地位无关。[29]这一点是需要读者认真体味的。
针对哲学结构的传统模式,特别是针对笛卡尔的“树喻”,莱布尼茨做了大量的拨乱反正、推陈出新的工作。首先,莱布尼茨藉“知识海洋论”一笔否认了传统哲学结构太过简单化和立体化的倾向。如果说毕达哥拉斯的“还原论”是西方哲学结构简单化和立体化迈出的第一步的话,则笛卡尔的“树喻”则显然把这样一种倾向进一步系统化和形象化。为了从根本上颠覆这样一些传统观念,莱布尼茨破旧立新,明确提出了“哲学知识海洋论”,为哲学各分支学科的互通互融及其平面化进行了论证。例如,早在1679年左右,莱布尼茨就在《奥秘的百科全书导论》中提出了“哲学知识海洋论”,断言不管你如何划分哲学或“普遍科学”,不管你断言它包含什么“分支学科”都无所谓,因为这些分支学科“就像海洋一样是个连续整体”。[30]1690年,莱布尼茨在《人类学说的视域》一文中,把这一点讲得更为生动。他写道:“各门科学的整体可以看作一个大洋,它到处延伸,毫不间断,从无间隔,尽管人们想象其中存在有许多部分,并按照自己的便利给它们以各种名称。”[31]1704年,在阐述“科学分类”时,莱布尼茨又重申了他的“哲学知识海洋论”,把“我们知识的全体”说成是“一个连成一片的海洋(un Oceean, qui est tout d’une piece)”。[32]
其次,针对笛卡尔的“树喻”从整体主义原则出发片面强调哲学各分支学科的有机统一性,莱布尼茨强调了哲学的学科分际,特别是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的学科分际。例如,在《人类理智新论》第4卷第8章里,莱布尼茨就明确地以“实践”和“理论”来概括“道德学”与“形而上学”的本质特征,断言:“真正的道德学之于形而上学的关系,就是实践之于理论的关系(la vraye Morale est à la Metaphysique, ce que la practique est la Theorie)。”[33]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莱布尼茨在第4卷第17章里,进而强调了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的“区分”,断言:“在必须用来支持我们知识的东西与可以用来作为我们已被接受的学说或作为我们实践基础的东西之间做出区别非常必要。”[34]在《神正论》里,莱布尼茨藉“两个著名迷宫(deux labyrinths famoux)”的说法,把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的学科分际鲜明不过地昭示出来了。因为所谓“连续体迷宫”或者说“连续体和看来是其要素的不可分的点的争论”无非是莱布尼茨理论哲学致力解决的根本问题,所谓“前定论”或“必然—自由”的“迷宫”则无非是莱布尼茨的实践哲学致力解决的根本问题。而莱布尼茨也正是在探索“连续体迷宫”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可分的“形而上学的点”即他所谓的“单子”,进而构建了他的形而上学体系即“单子论”,从而提供了走出“连续体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同样,莱布尼茨也正是在探索“前定论迷宫”或“必然—自由迷宫”的过程中区分了“绝对必然性”和“假设必然性”(以及“道德必然性”),批判了“懒惰诡辩”,比较全面和深入地论证了人的自由与善,构建了西方近代哲学史上第一个基于理性主义原则的以人的自由为中心内容的实践哲学体系,从而提供了一条走出“前定论迷宫”或“必然—自由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正因为如此,莱布尼茨不仅从实践哲学和理论哲学两个维度对于自己的哲学事业做出了概括,而且也从这样两个维度对自己的哲学成就予以相当自信的肯定,断言:“如果连续体的知识对于思辨的探索是重要的,则必然性的知识对于实践运用便同样重要。”[35]
在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学科分际问题上,莱布尼茨还有一项特殊贡献,这就是莱布尼茨从认识论和真理观上对这样一种分际做了相当深入细致的论证和阐释。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虽然从“静观思维”和“实践思维”与“认识性”和“计算性”等维度对理论科学和实践科学的“区分”做出了说明,但对这样一类“区分”的说明还是相当粗疏的。莱布尼茨作为一位著名的近代哲学家,乘近代西方哲学的中心由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之大势,从认识论,特别是从真理观上对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学科分际做了相当精细的诠释。例如,莱布尼茨将真理二分为“普遍真理”与“个别真理”、“推理真理”与“事实真理”、“必然真理”与“偶然真理”以及“第一真理”、“言说现实存在事物的真理”与“假设真理”等都是与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的学科分际直接相关的。[36]不难看出,其中“普遍真理”、“推理真理”、“必然真理”和“第一真理”都与理论哲学或“认识原则”直接相关,而“个别真理”、“事实真理”、“偶然真理”、“言说现实存在事物的真理”和“假设真理”则都与实践哲学或“实践原则”直接相关。还有,莱布尼茨的真理观不仅具有认识论的意义,而且还具有显而易见的本体论和逻辑学意义。就本体论而言,上述各类真理不是与可能性、可能存在、必然性、理性和知直接相关,就是与现实性、现实存在、偶然性、意志和行直接相关;就逻辑学而言,莱布尼茨断言:上述各类真理不是建立在矛盾原则或矛盾律的基础之上,就是建立在充足理由原则或充足理由律的基础之上:凡是与理论哲学直接相关的真理,或者说凡是与可能性、可能存在、必然性、理性和知直接相关的真理,如“普遍真理”、“推理真理”、“必然真理”和“第一真理”等,都是建立在矛盾原则或矛盾律的基础之上的;反之,凡是与实践哲学直接相关的真理,或者说凡是与现实性、现实存在、偶然性、意志和行直接相关的真理,如“个别真理”、“事实真理”、“偶然真理”、“言说现实存在事物的真理”和“假设真理”等,则都是建立在充足理由原则或充足理由律的基础之上的。毋庸讳言,即便亚里士多德也曾从真理观的角度审视过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的学科分际。例如,他在《形而上学》里,就曾明确指出:“把哲学称作真理的知识也是正确的。因为理论知识的目的是真理,实践知识的目的则在于其作用。”[37]不难看出,无论是从内容的丰富性还是从表达的精确性看,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与莱布尼茨的真理观都有明显的差距。因为将“实践知识的目的”界定成“理论知识”所追求的“真理”的一种“作用”,非但不能是我们精确地区分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反而模糊了二者的界限,将实践哲学降低成理论哲学的一门“应用学科”,成了一门“哲学应用学”。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莱布尼茨针对笛卡尔的“树喻”,明确地提出了实践哲学重于或高于理论哲学的原则,而且他还是在他的两个大部头哲学著作,即《人类理智新论》和《神正论》里提出这项原则的。
1704年,莱布尼茨在《人类理智新论》里在阐释“有无天赋实践原则”时就明确地提出了“道德比算术更重要(la morale est plus important que l’Arithmetique)”这样一个论断。[38]为什么道德会比算术“更加重要”呢?莱布尼茨解释说:这是因为作为实践科学的“道德科学”与作为理论科学的“算术”虽然都是一种“推证科学”,但它们的研究对象却大相径庭:“算术”是一种研究“数”的性质及其“运算”的科学,它归根到底与“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一样,是一门研究“物性”的科学,或者说是一门“理论科学”;而“道德科学”作为“实践科学”的一种,它本质上是一门研究“人性”或关于人的“实践活动”的科学,一门“劝善规过”从而“使人幸福”的科学。正因为如此,不管“算术”对于人类生活多么重要,它都只不过是人类谋取自身幸福的一种手段和工具而已。其次,莱布尼茨还从自然法的高度,对道德的特别重要性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佐证,这就是人类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趋乐避苦”的“道德本能”。在莱布尼茨看来,道德科学作为一门“推证科学”也和“算术”一样,无疑“同样依赖于内在的光”所提供的“推证”。不过,“由于这些推证并不是一下跳到眼前来的,所以,如果人们不是永远立即察觉到那些自己心中具有的东西,并且不是很快地就能读出……上帝刻在人们心里的那些自然法的字迹”。[39]但离开了一定的道德规则和社会规则,不仅人类的生存难以为继,而且整个社会也难以为继。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局面,上帝在创造人类时,便将“趋乐避苦”的道德本能一并赋予了人类。这样一来,人类便“得以立即并且不必经过推证就能处理理性所要求的某些事情。这就像我们走路是按照力学的规律的,但并没有想到这些规律,又如我们吃东西,不仅因为这对我们是必要的,而且还更多地是因为这使我们感到愉快”。[40]诚然,仅仅依靠这种道德本能尚不足以使我们获得幸福,因为这只能使得我们获得“一时”的或“当下”的快乐,而不可能获得作为“幸福”的“持久快乐”。而为要获得作为“幸福”的“持久快乐”,我们就必须进而借助于“理性”和必要的“推证”,形成种种道德规则乃至道德科学。[41]毫无疑问,这种道德规则和道德科学是一种理性化了的改造提升了的道德本能,但倘若没有“趋乐避苦”的道德本能则它们便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便永远不可能产生出来。由此足见“趋乐避苦”的道德本能以及道德和道德科学对于人类及其幸福生活的不可或缺性及其对于算术的优越性。在讨论莱布尼茨的“道德比算术更重要”这个论断时,还有一点需要强调指出,这就是:在莱布尼茨眼里,“算术”不仅具有“数学”的意义,而且还具有符号逻辑学的意义乃至本体论的意义。早在1666年,莱布尼茨在《论组合术》里,就不仅将他的“组合术”或“组合科学”说成是一种“纯粹的算术”,而把“位置几何学”或“关于位置的科学”说成是“一种关于图像的算术”,并且还进而强调说:“就其本身看,两者均属于形而上学”。[42]此后,于1679年,莱布尼茨在《达致普遍字符》一文中,又进而强调指出:“数似乎可以说是一种基本的形而上学模型或符号(numerus quasi fidura metaphysica est),而算术则是一种宇宙静力学(Statica Universi),事物的各种力都可以藉它发现出来。在数里面隐藏了最深奥的秘密(maxima in numeris mysteria)。”[43]既然如此,莱布尼茨的“道德比算术更为重要”的论断,显然就内蕴有道德(更不用说整个实践哲学)比整个理论哲学“更为重要”的意义。
此后,1710年,莱布尼茨在《神正论》里以“两个著名迷宫”的名义不仅把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学科分际鲜明地昭示了出来,而且还把实践哲学的优越性鲜明地表达出来了。在这里,莱布尼茨是用社会覆盖面作为审视和比较实践哲学和理论哲学的价值尺度的。莱布尼茨毫不含糊,他旗帜鲜明地写道:“自由与必然的大问题”“几乎困惑着整个人类”(embarrasse presque tout le genre humain),而“连续体和看来是其要素的不可分的点的争论”“则只是让哲学家们费心”(n’exerce que les philosophes)。[44]很显然,倘若仅仅着眼于社会覆盖面,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完全不成比例。难怪莱布尼茨在谈到“自由与必然”这个问题时用了“大问题(la grande question)”(la grande question)这个措辞。[45]那么,“自由与必然”这个问题为何竟至““几乎困惑着整个人类”?按照莱布尼茨的说法,这首先是因为“几乎整个人类”都对“必然性”做了“简单化”和“片面化”的理解,都将其理解成“绝对必然性”(la nécessité absolue),从而都身陷“自由与必然”的“迷宫”而不能自拔。因为按照人们对“必然性”的这样一种理解,“如果未来是必然的,那么,无论我做了什么,将要发生的一切也还是必将发生”。[46]既然如此,人们便“倾向于放弃一切行动,或者至少倾向于对于一切都漫不经心,而只任凭及时行乐的意愿”。[47]这样一来,人们便由于身受“懒惰理性(la raison paresseuse)”诡辩之“迷惑”而完全陷入“命运的必然性(nécessssité du destin)”,从而毫无自主自由可言,堕落成与动物无异的物种。但这些人所理解的“必然性”或“绝对必然性”无非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数学必然性”、“几何学的必然性”、“逻辑的必然性”和“形而上学的必然性”,而所有这些种类的必然性都有一个“共性”,这就是它们都是“理论哲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对象,而非“实践哲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对象。构成人的实践行为或自由行为基本原理的则是“假设的必然性”(la nécessité hypothétique)和“道德的必然性”(la nécessité morale)。几乎整个人类之所以对“自由与必然”这个大问题“困惑”不已,最根本的就在于人们在理解和解释人的实践行为或自由行为时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用了解释物的普遍必然性的哲学原理来解释人的实践行为或自由行为。因此,在莱布尼茨看来,人类走出“自由与必然”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不是别的,就是“物归其所,物尽其用”,也就是说:我们应当用“绝对的必然性”去思考那些“认识性的东西”或“存在者中那些其本原不可以是别样的东西”,而用“相对的必然性”来思考那些“筹划或计算”的东西,来“思考、筹划和计算”“那些是别样的东西”。[48]
既然哲学说到底是一种人学,既然人的自由及其自由行为不仅是人的本质规定性,而且是人的完满性或趋向完满性的根本表征,是提升人的完满性、达致人的幸福的根本途径,既然依据莱布尼茨的“必然性”学说,尤其是他的“假设的或道德的必然性学说”,“自由的行为中存在着一种超越迄今为止所能设想的完满的自发性(il y a dans les actions libres une parfait spontanéité, au-delà de tout ce qu’on en a conç jusqu’ici)”,[49]则莱布尼茨对“必然性”的二分及其“道德必然性”学说的提出,不仅突破了毕达哥拉斯的“还原论”和笛卡尔的“树喻”的根本局限,不仅深化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学科分际说,而且还超越亚里士多德,把实践哲学的学科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实践哲学的后世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因为很难想象,在哲学中还有什么能够比批驳“懒惰诡辩”、理性地张扬和阐释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由行为更为重要的东西了。
既然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由行为是莱布尼茨为我们提供的走出“自由与必然”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既然自由是其实践哲学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则“自由”也就势必构成其实践哲学的中心范畴。正因为如此,自由也就成了莱布尼茨毕生探索和阐述的一个重要线年,莱布尼茨就在《上帝的全能、全知和人的自由》一文里从神人关系的角度讨论了“人的自由”问题。[50]1680年左右,莱布尼茨又撰写了《论自由与可能性》一文,不仅从“必然事物的原则”和“偶然事物的原则”的高度对“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学科分际做出了高屋建瓴的说明,不仅强调指出:“几乎不容置疑,每个人都有自由做他意欲的事情”,[51]而且还对自由做出了明确的界定。此后,莱布尼茨又于17世纪80年代末,写出了《论自由》和《自由与同理性结合在一起的自发性》两文,不仅把“自由与偶然性如何同因果系列与天道共存”说成是“困扰着人类的一个最古老的问题”,直言“人类心灵有两个迷宫”:一个关涉连续体的组成,另一个关涉“自由的本性”,[52]而且还从“理性”和“自发性”两个维度来界定“自由”。[53]1704年,莱布尼茨在《人类理智新论》里,在与洛克的论战时特别突出了“自由”问题。依据格本,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作为莱布尼茨的认识论专著,正文计68章,计448页,章均不到6.6页,但讨论“自由”的第2卷第21章却是该著中最长的一章,竟有42页之多,[54]其篇幅是一般章节的6倍多,由此便足可看出他对于自由问题的格外重视。至于莱布尼茨于1710年出版的《神正论》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有理由称之为一部研究“自由”的学术专著,因为它虽然也讨论了“上帝的自由”,但它之所以讨论“上帝的自由”,其根本目的也在于比喻和阐释“人的自由”。至于本论文集所收集的20多篇论文,可以说几乎没有一篇与自由无关。其中,《自然法原理》、《论德意志王权的至上性》、《作为上帝形象的国君的肖像》、《论法与正义的概念》、《论作为幸福科学的智慧》、《关于人的自由与恶的起源的对话》、《政治学的目标、混合政体与自由》、《对正义公共概念的反思》、《对普芬道夫原则的看法》以及《评1711年出版的论人》等对自由的论述尤为精辟。莱布尼茨对于他在自由问题上所做的种种思考,特别是他在《神正论》里对自由所做的全面、系统、深入的思考非常看重,将其视为他哲学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颇有几分自得之乐,以至于直至其生命的最后阶段(1716年8月中旬,他是于当年11月14日去世的),当谈到他的《神正论》这一大部头著作的主题时,莱布尼茨还不无自信地宣布:“也许没有人比我在《神正论》中更好、更深入地解释过自由、偶然性、自发性”及其与“绝对必然性、命运机遇、强制”之间的“线]
应该说,在莱布尼茨思索和阐释“自由”范畴的漫长生涯中,他曾对“自由”做出了种种不同的界定。例如,他于1680年左右,在《论自由与可能性》一文里就从“自发性”、“理性”(充足理由律)和“偶然性”三个维度来界定“自由”。[56]此后,莱布尼茨在《自由与同理性结合在一起的自发性》一文里,直截了当地将“自由”界定为“同理性结合在一起的自发性(spontaneitas intelligentis)”。[57]1704年,莱布尼茨在《人类理智新论》里,不仅把“自由”界定为“自发性”和“深思熟虑(deliberees)”,而且还把“自由”界定为“能够以别的方式行事”。[58]在《神正论》里,莱布尼茨在继承亚里士多德“自由观”的基础上,[59]给“自由”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断言:“自由,……就在于理性(l’intelligence),……在于自发性(la spontanéité),……以及在于偶然性(la contingence)”。[60]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莱布尼茨给“自由”所下的有关“自由”的所有上述定义,虽然有时也有所侧重,但就其基本意涵来说,可谓小异而大同,也就是说,他所下的“自由”定义虽然措辞略有差异,但其真实的内蕴却无不具有下述三点,这就是“理性”、“自发性”和“偶然性”。例如,莱布尼茨既然在《论自由与可能性》一文里既讲到了“自发性”,又讲到了“理性”(充足理由律)和“偶然性”,则他在这篇论文里所使用的“自由”概念,就显然与他在《神正论》里所使用的“自由”概念,没有任何原则上的区别。[61]至于莱布尼茨在《自由与同理性结合在一起的自发性》一文里,将“自由”界定为“同理性结合在一起的自发性”,从字面上看,似乎与莱布尼茨关于“自由”的三要素说有别,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他紧接着便说:“自发性是没有强制的偶然性(Spontaneitas est contingentia sine coactione)”。[62]而这就意味着,莱布尼茨在这里所给出的“自由”定义,尽管从字面上看似乎与“偶然性”无关,但在事实上却内蕴有“偶然性”。莱布尼茨在《人类理智新论》里,虽然从字面上看,他确实曾把“自由”界定为“自发性”和“深思熟虑(deliberees)”,但就其本质内容看,所展现的依然是自由的三要素。因为,莱布尼茨在《人类理智新论》第2卷第21章第9节里,在将“自由”直接界定为“自发性”和“深思熟虑”(亦即“理性”)之后,紧接着就讲到了“偶然性”和“偶然线]更何况莱布尼茨在该著第4卷第17章第4节里还曾明确地把“自由”界定为“能够以别的方式行事”,断言:“凡本来能够以别的方式行事的都是自由的(qui a pu faire autrement a esté libre)”。[64]即使在《神正论》里,当莱布尼茨在援引和阐释亚里士多德的“自由观”时,也是立足于他的“自由”三要素说的。例如,莱布尼茨在《神正论》“上篇”第34节援引亚里士多德的“自由观”时,虽然只论及“自发性”和“选择”,但既然为要进行选择,就不仅需要“理性”,而且还需要“偶然性”。因此,在莱布尼茨看来,他的这个说法中就已经蕴含了自由三要素了。更何况这种情况并不只是笔者的一种猜测,而是莱布尼茨的真实意图。因为莱布尼茨在本节之内紧接着就提到了“偶然性”和“判断力”。他写道:“在形形的自然行为中都存在有偶然性;但如果行动者没有判断力,也就没有自由。”[65]莱布尼茨在这句话里所说到的“判断力”所意指的无疑就是“理性判断力”,就是“理性”。综上所述,莱布尼茨有关“自由”的说法虽然多种多样,但他的任何一种说法中,其实都内蕴有“理性”、“自发性”和“偶然性”三种意涵或三种要素,正因为如此,我们把莱布尼茨在《神正论》“下篇”第288节里给“自由”所下的定义称作“经典”,也正因为如此,当我们阐释莱布尼茨的“自由”范畴时,就应当从莱布尼茨的自由三要素或自由的三重根谈起。
在谈到自由三要素或三重根在其自由范畴中的理论地位时,莱布尼茨曾明确地分别将理性、自发性和偶然性说成是“自由”的“灵魂”(l’ame)、“主体(le corps)”和“基础(la base)”。[66]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先谈“偶然性”问题。因为“偶然性”是自由的“基础”,既然离开了偶然性这个基础,自由就成了无本之木或无源之水,我们讨论自由自然就绕不开偶然性这个话题。而且,如果我们不谈偶然性,只谈必然性(绝对必然性),那就不仅不可能有个人自由,而且也就压根没有自由这回事。正因为如此,莱布尼茨明确地将“偶然性”界定为“对逻辑的和形而上学的必然性的排除”。[67]在莱布尼茨看来,“必然性”有两种:一种叫“绝对的必然性”,另一种叫“相对的必然性”。在实践哲学领域,莱布尼茨要“排除”的“逻辑的和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属于“绝对必然性”,而他竭力提倡的“假设的必然性”和“道德的必然性”则是一种“相对必然性”。它们的根本区别在于:绝对必然性侧重的是人类的“知”,它遵循的是逻辑的“矛盾原则”,其昭示的是事物的普遍本质,旨在构建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体系,亦即旨在构建理论科学或理论哲学;而相对必然性侧重的则是人类的“行”,它遵循的是“确定理由原则”或“充足理由原则”,其昭示的是事物的现实存在及其变化,旨在构建不断完善人类自己且不断促进人类幸福的实践哲学。毋庸讳言,既然一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在理论科学或理论哲学中,我们思考的是“存在者中那些其本原不可以是别样的东西”,亦即“那些其本原”为“绝对必然性”的东西,则思考和运用“绝对必然性”就是理论科学或理论哲学的“分内之事”。但既然实践科学或实践哲学与理论科学或理论哲学各有自己的本体论、认识论、真理观和逻辑原则,我们倘若越俎代庖,将“绝对必然性”原则挪用到实践科学或实践哲学领域,那就势必使原本为理论科学或理论哲学有效运用的“绝对必然性”原则“不折不扣地变成了普洛克禄斯特的胡床”,[68]这样一种蛮干行为不仅全然肢解了人的自由行为,摧毁了人的道德尊严,而且也极大地破坏了“绝对必然性”的声誉。无怪乎莱布尼茨要将“偶然性”说成是“自由的一种典型特征(un attribut caractéristique de la liberté)”。[69]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就曾强调指出了“偶然性”的“道德价值”,[70]但由于长期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对必然性的偏爱,许多西方哲学家不仅无视偶然性的存在,而且还将对偶然性的承认视为对必然性的无知,[71]莱布尼茨可以说是西方近代第一个不仅承认偶然性存在,不仅强调偶然性的道德价值,而且还对偶然性的自由价值和实践哲学价值做出了系统深入说明的重要哲学家。从前面所说的看来,偶然性之所以能够构成自由的“基础”和“自由的典型特征”,最根本的就在于偶然性给我们的自由选择提供了“可能”。但给我们的自由选择提供了可能这样一种说法的真正意蕴又是什么呢?这岂不是说我们面前存在有两个乃至多个选项,而且这些选项不是有待生成的,而是现成的或者说是被给予的。倘若没有这样一些现成的或被给予的选项,我们的自由选择无疑就会变成一种空谈。莱布尼茨之所以反复强调自由选择的“确定理由原则”,很可能出于这样一种考虑。用模态逻辑的语言说就是:由“a偶然是b”可以推导出下述两个模态命题:“a可能是b”与“a可能不是b”。这就是说,在“a偶然是b”的情况下,无论你选择“a可能是b”还是“a可能不是b”同样都不矛盾,都被允许。这就是“偶然性”、“道德必然性”和“自由选择”的秘密所在。这也就是说,莱布尼茨所说的偶然性,既有别于绝对必然性,也有别于绝对任意性或纯粹偶然性,从而我们既要一方面看到这样一种偶然性“并不妨害人们对于其所选择的方面具有更强的倾向”,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它也“并不要求人们对两个相反的方面采取绝对和同等的无差别的立场”。[72]所有这些都是需要读者认真体味的。
既然在莱布尼茨这里,“偶然性”并不是一个“意外事件”,而是自由主体的一种“意内事件”,离开了自由主体对种种选项的认知、评估、选择、决断和实践行为,偶然性便不复为偶然性,既然他所谓“自发性”即是自由的“主体”,则我们在初步考察过偶然性之后,就有必要转而考察莱布尼茨自由观的另一个要素——“自发性”了。自发性既是一个有关自由主体的本质规定性问题,也是自由活动的内在源泉问题。在谈到“自发性”时,莱布尼茨强调“自发性,……就其为我们自身内部所固有构成我们活动源泉的东西而言,它属于我们”,他还进而强调指出:“我们的自发性不容许有任何例外,从严格的哲学意义上讲,外在事物对我们并无任何物理的影响”,[73]即是谓此。其实,倘若我们考虑到莱布尼茨的实体学说,即他的单子论,人的自由行为的自发性就一点也不难理解了。既然单子既不是物理学的点,也不是数学的点,而是不可分的形而上学的点,既然单子即是形而上学的力的中心,既然单子没有与外界联系的“窗户”,既然能动性是单子的本质规定性,我们便有理由像莱布尼茨那样宣布:“真正的自发性是我们和简单实体所共有的,它在理性实体或自由实体中则构成其行为的主宰,……(我们的)灵魂自身有一种完满的自发性,以至于在其活动中它仅仅依赖……它自身。”[74]也正因为如此,莱布尼茨才明确地将我们的行为自由或行为自主的可能性完全归因于我们行为的“自发性”,断言:“亚里士多德就曾经给它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当一个行为的源泉在行为主体身上时,这个行为就是自发的(‘Spontaneum est, cujus principium est in agente’)。但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的一切活动和意志活动才完全依赖我们。”[75]
其实,亚里士多德不仅给“自发性”下了上述定义,而且还对照偶然性对自发性的有关属性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他指出,自发性虽然和偶然性一样,“也属于原因”,也“属于原因中‘变化的根源’一类”,但它与偶然性不同,既没有“确定的意图和思考”,也与“道德价值无关”,从而“可以出现于许多低等动物和许多无生物之中”。[76]亚里士多德还从词形学的角度对自发性的涵义进行了阐释。他指出:“自发(αυτοματον)这个词中的‘无目的(ματον)’即说明了它的涵义。它所使用的场合是‘所为的某行为’(目的)没有发生,只发生了达到目的的手段。……因此,自发(αυτοματον)这个词就其词源而言,意思就是:自身(αυτο)无目的地(ματον)发生。例如,石头掉下来打了一个人,并不是因为要打他这个人而掉下来的,所以它是自发地掉下来的,但它也可以是由于一种要打击的目的而掉下来的。”[77]由此看来,莱布尼茨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自发性无非是一种自然禀赋或本能。但是,问题在于:既然他所谓自发性意指的只是一种自然禀赋或本能,则莱布尼茨为何会将自发性视为自由的“主体”呢?而且既然如上所说,自发性即意味着“无目的性”和“无道德性”,它如何能够构成从事有意识、有目的且具有道德性活动的人的自由行为的“源泉”呢?应该说,莱布尼茨对所有这些问题都做出了比较充分的说明。例如,在《人类理智新论》第1卷第2章,莱布尼茨在为“天赋的实践原则”进行辩护时,就特别强调了本能的道德价值。他明确指出:“因为道德比算术更加重要,所以上帝给了人那些本能,使人得以立即并且不必经过推证就能处理理性所要求的某些事情。这就像我们走路是按照力学的规律的,但并没有想到这些规律,又如我们吃东西,不仅因为这对我们是必要的,而且还更多地是因为这使我们感到愉快。但这些本能并不是以一种不可克服的方式来促使我们行动的;我们得以情感来抗拒它们,以成见来模糊它们,以相反的习惯来改变它们。可是我们最通常的情况是符合这些良心的本能,并且当更大的印象并没有压倒它们时也还是顺从它们。人类之中最大部分和最健康部分可以为之作证。”[78]这可以视为莱布尼茨对本能道德价值的一个经典的说明!因为莱布尼茨的这段话相当明晰地告诉我们:尽管本能尚不是道德原则或实践原则,更不属于道德科学或实践哲学,但是各种道德原则或实践原则乃至各种道德科学或实践哲学也都可以以这样那样的形式从本能中生发出来,这就有力地论证了自发性或本能乃“我们自身内部所固有、构成我们活动源泉的东西”。我国古代哲学家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早在2400多年前就曾说过:“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79]他的这段话中所说的“才”,更具体地说,他的这段话中的为朱熹称之为“仁义礼智之端”的“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即是莱布尼茨所说的“自然禀赋”或“本能”;而孟子所说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所强调的显然也正是莱布尼茨所说的自发性或本能乃“我们自身内部所固有构成我们活动源泉的东西”。由此足见,东圣西圣,其揆一也。
莱布尼茨虽然强调“自发性”或“本能”构成了我们自由活动的“源泉”或一个要素,却并没有因此而将其视为自由或自由活动本身。在《人类理智新论》里,莱布尼茨曾对这个问题做过一些比较具体的说明。首先,莱布尼茨认为人的行为自由虽然与我们的自然禀赋或本能相关,但它直接涉及的是人的内蕴有理性因素的“意欲”而非作为“本能”的我们并未“察觉”的“欲望”。他解释说:所谓“意欲”,是“趋向人们觉得好的和远离人们觉得坏的东西的努力或倾向,所以这种努力或倾向是人们对它们察觉的直接结果”,至于“那些由我们没有察觉的、感觉不到的知觉来的努力,我宁愿称之为欲望(appétitions)而不叫做意欲(Volitions)(虽然也有一些欲望是可以察觉的)”。[80]其次,与此相关,莱布尼茨认为本能(包括“同情”和“反感”等)虽然不仅是“我们自身内部所固有构成我们活动源泉的东西”,不仅具有在人的自由实践活动中具有“绝对必然性”所内蕴的那样一种强制性倾向的积极作用,但它与理性毕竟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禀赋,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认识形态:其中本能、同情或反感等只具有一种混乱模糊的知觉或认识,而理性则具有一种清楚明白的知觉或认识。莱布尼茨说:“所谓本能就是一个动物不知其故地趋向适合于它的东西的一种倾向”,[81]即是谓此。但是,这样一种倾向既有可能符合指导我们选择活动的“最佳原则”,也有可能不符合“最佳原则”。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就应当扬弃本能所趋向的那样一种倾向,以实现我们所意欲的后果。鉴此,为了使我们的行为达到真正的自由,并实现我们所意欲的目标,我们的本能就必须允许理性进行“矫正性干预”:不仅允许理性利用和驾驭本能,而且允许理性充实、修正乃至扬弃本能。由此,我们便达到了自由的第三个要素,即“理性”。
对于莱布尼茨来说,“理性”固然与“偶然性”和“自发性”一样,也是他的自由观中的一个构成要素,但又与后者有别,是一种既与“偶然性”又与“自发性”密切相关的东西,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这两个要素中的要素:倘若撇开“理性”,不仅“偶然性”会因此而变成一种纯粹的“意外事件”,而且“自发性”也会因此而变成一种“动物本能”、“激情”、“微知觉”和“赤裸裸的意志”。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莱布尼茨把理性说成是“自由的灵魂(l’ame de la liberté)”。[82]具体地说,莱布尼茨主要是从“知识论”、“选择论”(“确定理由原则”和“最佳原则”)和“实践理性的具体性(有声思想论)”等方面来诠释自由的理性要素的。首先,莱布尼茨是从“知识论”的立场来理解和阐释作为自由要素的“理性”的。例如,在《神正论》里,莱布尼茨在诠释自由的“理性”因素时,即断言:“它包含了一种对深思熟虑对象的明确的知识(une connaissance distincte de l’object de la délibération)”。[83]其次,莱布尼茨强调人们为要进行自由选择,“在他们自己的国度里成为主宰”,他就必须充分利用他自己的理性。因为“他自己的国度就是理性的国度,他只要及时准备种种激情,他就能够遏制最猛烈激情的汹涌势头”。[84]莱布尼茨曾以奥古斯都处理费边将军一事来解说理性在自由选择中的重大作用。他写道:“他在下达处决费边·麦克西姆的命令时,按照他的习惯,遵照一位哲学家向他提出的忠告:当他在盛怒之下做一件事之前最好先行背诵一遍希腊字母。这样一种反思既挽救了费边的生命,也挽救了奥古斯都的声誉。”[85]事实上,莱布尼茨之所以提出“确定理由原则”和“最佳原则”,其目的都是为了帮助人们在进行自由选择时切实贯彻“理性”原则。莱布尼茨甚至强调说:“上帝的王国,智慧的王国,其实就是理性王国。”[86]其言外之意无非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获得充分的自由,我们就必须严格照理性办事,竭力构建我们的“理性王国”。不过,莱布尼茨虽然强调理性的自由功能,却也并未因此而一笔抹杀感觉和情感在人的自由活动中的积极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自由活动的根本目标无非是将某种可能的东西转变成现实的东西。然而,但凡现实的东西又总是具体的具有特殊性和个体性内容的东西,另一方面作为自由活动的主体为要实施必要的实践活动就不仅需要有理性知识而且还需要具有一定的热情。因此,莱布尼茨在实践科学中提倡具体理性,反对抽象理性,提倡普遍性、特殊性和个体性的三位一体,反对完全缺乏特殊性格和个体性内容的抽象普遍性,他将后者称作“排除实际解释的语词或记号所给予的一些无声的思想(les pensées sourdes)”。[87]强调实践理性的具体性、现实性和“有声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综合性”是莱布尼茨自由哲学和实践哲学的一项本质特征。
为了进一步阐释和强调他的自由观中理性因素的特别重要性,莱布尼茨两线作战,一方面反对和批判经验主义的自由观,另一方面又反对意志主义的自由观。针对经验主义的自由观,莱布尼茨强调我们只有借助于“清楚”的理性知识,我们才有可能在行动时“摆脱奴役”,获得“我们所期望的完整的精神自由(toute la liberté de esprit quiserait à souhaiter)”。[88]然而,感觉提供给我们的却只是一些“混乱的思想”,“当我们的知觉混乱时,我们就成了情感的奴隶”,我们便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能够给我们带来幸福的自由。诚然,尽管我们身处“奴役”状态时,也可以进行某种“自由选择”(un choix libre):“去选择那些在我们所处的状态下与我们当下的力量和知识相称的最使我们感到快乐的事物”。“但不幸的是:那些使我们感到快乐的东西却往往是一种实在的恶”。[89]笛卡尔虽然是西方近代理性哲学的奠基人,“在自由意志这个问题上”却如莱布尼茨所说,主张所谓“内感觉”,从而“陷入窘境”。他断言:“我们根据理性确信上帝的天道,但我们根据自身内部的经验同样确信我们的自由;我们必须相信两者,尽管我们看不到调和它们何以可能。”[90]笛卡尔还鼓吹意志自由主义,不仅强调“我们自由行为的独立性”,而且还特别强调了上帝自由的绝对性。在《第一哲学沉思集》里,当谈到“自由意志自由”和“上帝的自由”时,断言:“上帝的意志对已有的或者将要有的一切”“亘古以来”“就是无所谓的”。他以三角形为例解说到:“就是因为他(指上帝——引者注)愿意一个三角形的三角之和必然等于二直角,所以它现在就是这样,并且不可能不是这样。”[91]在谈到笛卡尔的“内感觉”理论时,莱布尼茨指出:“即使笛卡尔先生所提出的以他所谓灵敏的内感觉(un prétendu sentiment vif interne)来证明我们自由行为的独立性的理由也毫无力量。”[92]他解释说:“严格地讲,我们感觉不到我们的独立性,我们也不总是能够意识到我们的决断所依赖的那些常常知觉不到的原因。”[93]他举例说:“这就好象磁针高兴指向北方一样,它自以为它之转动独立于任何别的原因,这是由于其没有意识到磁针材料知觉不到的运动的缘故。”[94]至于笛卡尔的“无所谓”态度,莱布尼茨无论在阐述自由的“偶然性”因素时,还是在阐述自由的“理性”因素时,都将其视为他的一个主要的批判靶子。例如,在《神正论》的“前言”里,莱布尼茨就断然指出:“在自由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无所谓或漠然态度(une indifférence dans la liberté)。”[95]在《神正论》“上篇”里,针对笛卡尔等人的“无所谓”态度,莱布尼茨又特别提出和论证了“确定理由原则”。莱布尼茨强调说:“我们的推理有两条大原则。一条是矛盾原则(le principe de la contradiction)”,“另一条是确定理由原则(le principe de la raison déterminante)”。[96]所谓“确定理由原则”,其说的是:“任何一件事物如果没有一个原因,或没有至少一个确定的理由,它就永远不可能产生。也就是说,任何一件事物如果没有它之所以存在而不是非存在,是这样存在而不是那样存在的先验的理由,就永远不可能产生出来。这条大原则适用于所有的事件,永远找不到反面的例证。”[97]这就意味着莱布尼茨将笛卡尔等人有关自由的“无所谓”态度或立场从他的自由观中彻底剔除了。
自由,作为实践哲学的中心范畴,其在莱布尼茨实践哲学中的地位无疑举足轻重,但在莱布尼茨实践哲学体系中还有一个更为根本或更为基础的东西,这就是莱布尼茨的自然法概念。
自然法一词并非莱布尼茨的发明,可谓源远流长。有学者甚至将其上溯到西方哲学的源头,亦即上溯到希腊自然哲学,上溯到米利都派和爱菲斯派。这样一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按照英国哲学家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的看法:“一个事物的自然就是使它像它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行为的东西。”[98]希腊自然哲学中的“自然”(φνοις)既然所意指的即是万物的“本性”、“本质”、“始基”或“逻各斯”,则它与“自然法”中的“自然”也就因此而一脉相承。但是,真正说来,“自然法”概念的真正源头既非米利都派,也非爱菲斯派,而是具有人文倾向的智者希庇亚。因为希庇亚(Hippias)不仅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了“自然法”概念,而且第一个将“人的自然(本性)”从“物的自然(本性)”中剥离出来,进而将依据和合乎“人的自然(本性)”的“自然法”与“约定的”或“人造的”成文法对立起来,并且用“正义”和“不义”来界定“自然法”和“约定法”。[99]其后,自然法的概念虽然也与时俱进,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迁,但无论是在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还是在古罗马法学家那里,无论是在中世纪神哲学家托马斯那里,还是在近代法学家格劳秀斯那里,自然法的概念都无不带有希庇亚赋予的人性论印记。
在西方自然法观念的变迁史上,莱布尼茨享有特殊的地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不仅是因为莱布尼茨像当年的希庇亚那样坚持从人性论而不是从物性论的立场来看待自然法,也不仅是因为莱布尼茨在西方法学史上第一个从法哲学的立场来看待自然法,更根本的则在于莱布尼茨从实践哲学的高度看待自然法,视自然法为整个实践哲学的第一原则。
早在1670—1671年间,莱布尼茨就在《自然法原理》一著中突出强调了遵照自然法行事对于我们谋取人类幸福的极端重要性。在他看来,为要遵照自然法行事,最根本的就是要认识我们自己作为理性动物的本性或本质规定性。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方能消灭“我们内部所隐藏的敌人”(intra nos hostis superest),即对我们自己本性的“无知”,我们方能构建起包括作为“有用科学”的“政治学”(Politica utilis)和作为“正义科学”的“伦理学”(Ethica justi)在内的种种实践科学,我们才能成为“世界的征服者”。[100]1693年,莱布尼茨在其发表的《万民法典档案汇编》(Codes Juris Gentium Diplomaticus)的序里,在谈到自然法的意义时提出了“法的原理(其意指的当是自然法原理)既然摆脱了大自然的严格限制,便为人类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领域”的著名论断。[101]不难看出,莱布尼茨在这里所说的“大自然”不是别的就是传统自然哲学里所说的“自然”,就是作为“物性”的“自然”,而他所说的“自然法”中的“自然”所意指的当是他的实践哲学中作为“人性”的“自然”,而他在这里所说的“人类的研究”也当是我们有关人类本性及其实践行为的研究,亦即我们对于种种实践科学的研究。这就清楚不过地表明:在莱布尼茨看来,自然法不仅是实践哲学的“总纲”,而且也可以视为种种实践科学的“总括”。莱布尼茨在其于1704年完成的《人类理智新论》里,在谈到人类知识部门的关系时,特别强调了自然法学的源头性和独立性,断言“自然神学和自然法学的基本原理(quelques rudimens de la Theologie et de la Jurisprudence naturelle)”是“既不依赖于人法,也不依赖于神法的(independentes des loix divines et humaines)”。[102]之后于1706年,莱布尼茨在其《对普芬道夫原则的看法》一文里,在论及自然法的崇高地位时,针对普芬道夫的狭隘经验论和情感主义立场,强调指出:若要“将所有的美德都奠定在普遍的正义的基础之上”,我们“不仅要靠我们自己,而且还要靠社会,但首先要靠的是通过上帝写在我们心里的自然法我们发现我们与上帝同在,靠的是我们不仅有一个充满自由思想的灵魂,还有一个生生不息的追求正义的意志”。他诘问道:“倘若不在自然法这门科学之中,我们应当到什么地方来考察这些确定地属于法和自然正义的题目呢?”[103]1710年,莱布尼茨在《神正论》里,当谈到“对一切人和在一切地方都有约束力的永恒法与只适用于某些时代和某些民族的实证法之间作出区分”时,他从理性主义和本质主义的立场出发(亦即从“事物的本质和第一原则的真理不可改变”的立场出发),直接援引了培尔《再论关于彗星的各种思考》第2卷第152章中的说法,将基于“永恒理性”的“自然法”称作他的实践哲学的“第一实践原则(des premiers principes pratiques)”。[104]
莱布尼茨不仅视自然法为他的实践哲学的“第一原则”,而且还进而从他的自然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两个维度对他的自然法概念作了比较深入和比较系统的阐释。
首先,莱布尼茨从反对极端神秘主义、意志主义和经验主义(情感主义)的高度阐释了他的自然法概念的理性主义本质。例如,早在1693年,莱布尼茨就在《万民法典档案汇编》的序里,将“具有理性本性的永恒法(永恒法权)”视作自然法的基本源泉。[105]之后,莱布尼茨在其于1704年完成的《人类理智新论》里,断然否定“自然法学的基本原理”对于“神法”的依赖。1706年,在《对普芬道夫原则的看法》一文里,针对普芬道夫将“法律”界定为“一道命令”的意志主义立场,莱布尼茨强调指出:“自然法在我们身上的动力因是永恒理性之光,这样一种光是由上帝在我们的心灵之中点亮的。”[106]1710年,莱布尼茨在《神正论》里针对普芬道夫所持守的“准意志决定论”立场,强调指出:“人们可以非常正当地说,自然法的规定预设了所规定内容的合理性和正义,践履其所包含的内容乃人的义务,即使上帝极其任性在这方面也并未作出任何规定。”莱布尼茨还进而指出:“既然藉事物的本性本身,并且在神法之前,道德真理就使人承担了一些义务,托马斯·阿奎那和格劳秀斯便十分正当地说道,哪怕没有上帝,我们也还是有义务照自然法行事(s’il n’y avait point de Dieu,nous ne laisserions pas d’être obligés à nous confermer au droit naturel)。”[107]由此可见,莱布尼茨的理性主义立场可谓坚定。
另一方面,莱布尼茨从自然法乃实践哲学第一原则的高度对作为“人类研究广阔领域”的实践哲学外延(或分支学科)的种种实践科学(或实践哲学)也进行了相当广泛和系统的阐述。就我们所接触到的而言,我们不妨将有关分支学科归结为“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和“宗教哲学”四大门类。诚然,实践哲学既然是一种研究人的本性及人类实践行为的科学,它就不会仅仅限于这样四个分支学科。例如,莱布尼茨就不止一次地提及“医学”。在《自然法原理》一著里,在谈到实践哲学学科的构建时,他首先提到的就是“医学”,并将医学称作“一门令人愉快的科学”,断言:“令人愉快的科学是医学(Iucundi scientia Medica est),有用的科学是政治学,正义的科学是伦理学。”[108]之后,他在《普遍科学序言》里,又明确地将“医学”与“伦理学、灵魂学说和神学”等学科一起,称作“普遍科学”,称作一门能够帮助我们“获得线]在《人类理智新论》里,在论及知识的分类时,他甚至呼吁改革西方传统的科学知识“三分法”(自然哲学、实践哲学和逻辑学),用“神学、法学、医学和哲学(de Theologie, de Jurisprudence, de Medecine et de Philosophie)”这“四大学科(les quatre facultés)”取而代之。[110]此外,莱布尼茨在《人类理智新论》里,还特别论及经济学,断言:“经济学包括数学和力学的技术以及一切有关人的生计以及生活便利等方面的细节,其中将包括农学和建筑学。”[111]事实上,莱布尼茨作为西方近代最著名的百科全书学者,他的研究几乎涉及他所在时代的实践哲学的所有领域。尽管如此,“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和“宗教哲学”在莱布尼茨的实践哲学体系中依然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理应得到更加充分的关注和阐释。但是,鉴于我们在《莱布尼茨宗教哲学与自然神学文集》(即《莱布尼茨文集》第9卷)里将对莱布尼茨的宗教哲学论著进行专门的编译和阐释,在本卷的“编译者序言”里,我们将依次仅对他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基本思想做一些扼要的说明。
在莱布尼茨的实践哲学体系中,道德哲学享有崇高的甚至其他实践哲学分支学科难以企及的地位。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说,首先是因为在莱布尼茨看来,道德学和道德哲学是自然法的应有之义。如前所述,自然法概念中的“自然”意指的无非是人的“自然”或“本性”。但人的“自然”或“本性”的内涵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不仅有“理性”的意蕴,而且还有“德性”的意蕴。如果说“理性”是人的“第一自然”或“第一本性”的话,我们则不妨将“德性”称作人的“第二自然”或“第二本性”。正因为如此,莱布尼茨在《对普芬道夫原则的看法》一文里,在论及“道德实践”(the practice of virtue)时,就曾将其称作人的“第二本性”(a second nature)。[112]诚然,一些普通的民法学家,甚至像普芬道夫那样赫赫有名的民法学家,在论及法律时往往“满足于人的外在行为”,以为法律“仅仅与物质对象相关”,而与人的“内在的东西”无关,与人的“充满自由思想的灵魂”和“追求正义的意志”无关,一句话,与“人的内在德性”无关,则这样一些缺乏“道德哲学意识”的人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些民法学家,而永远算不上“法哲学家”和“实践哲学家”,从而与“实践哲学”无缘。[113]其次是因为在莱布尼茨看来,“德性”问题不仅是法哲学或实践哲学的一个问题,也不仅是法哲学或实践哲学的一个层面,而且是法哲学或实践哲学的一个更为根本和更高层次的东西。莱布尼茨在谈到自然法的“等级”或“层次性”时,曾将自然法区分为三个等级,这就是“严格法(jus strictum)”、“衡平法(aequitas)”和“虔诚或正直(pietas vel probitas)”。它们的区别在于:严格法只是一种“法律要求(facultatem)”,正因为如此,它又被称作“纯粹法(Juris meri)”。而衡平法和正直则不同,“我们对于这些只有一种道德要求(aptitudinem),却没有法律要求(non facultatem)”。具体地说,衡平法要求的是“仁爱”(狭义平等的仁爱),而虔诚或正直要求的则是一种“普遍正义”。如果说严格法只不过是一种“维持和平的原则(principio servandae pacis)”,其宗旨在于“避免痛苦”,而衡平法和正直从根本上讲则是一种讲求德性的原则,其宗旨则在于谋求幸福。[114]第三,最为重要的乃是因为莱布尼茨在《人类理智新论》第4卷第21章里,竟使用了“实践哲学或道德(la Philosophie practique ou la Morale)”这样一种表达式。这就生动不过地表明,在莱布尼茨的心目中,“德性”问题或“道德”、“道德哲学”问题即使不是一个与“实践哲学”的同义或等义的问题,那至少也必定是个与之近义的问题,这就把“道德哲学”崇高的学科地位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了。
其实,道德哲学在莱布尼茨的实践哲学体系中之所以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充分体现了自然法的目的或宗旨。那么,在莱布尼茨看来,自然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对此,在《对普芬道夫原则的看法》一文里,莱布尼茨讲得非常清楚,这就是“旨在确保那些遵守自然法的人获得好处”。[115]那么,我们人从中获得的“好处”究竟有哪些呢?归根结底,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我们人自己的“幸福”,二是我们人自身的“完满性”及其“提升”。首先,幸福,我们人的幸福,即是自然法的目的和莱布尼茨道德哲学的目的。早在1670年,莱布尼茨在《自然法原理》里集中阐述了“人类的幸福(felicitatem generis humani)”问题,将“营造我们的幸福”视为我们的一项基本使命,呼吁我们自己“因人类大多数获得幸福而幸福”。[116]1693年,在《万民法典档案汇编》的“序”里,莱布尼茨又明确断言:“智慧无非是幸福科学本身(sapientiam nihil aliud esse dicamus quam scientiam felicitatis)”。[117]其后,他在《论作为幸福科学的智慧》一文里,又进一步解释说:“智慧无非是一门幸福科学(die Wissenschaft der glückfeeligkeit),或者说是一门教导我们如何获得幸福的科学。”[118]不仅如此,莱布尼茨还视“幸福科学”为一门首选科学,断言:“智慧是一门关于幸福的科学,从而也是一门必须先于所有其他事物予以研究的科学。”[119]据。